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幽灵支持对碳定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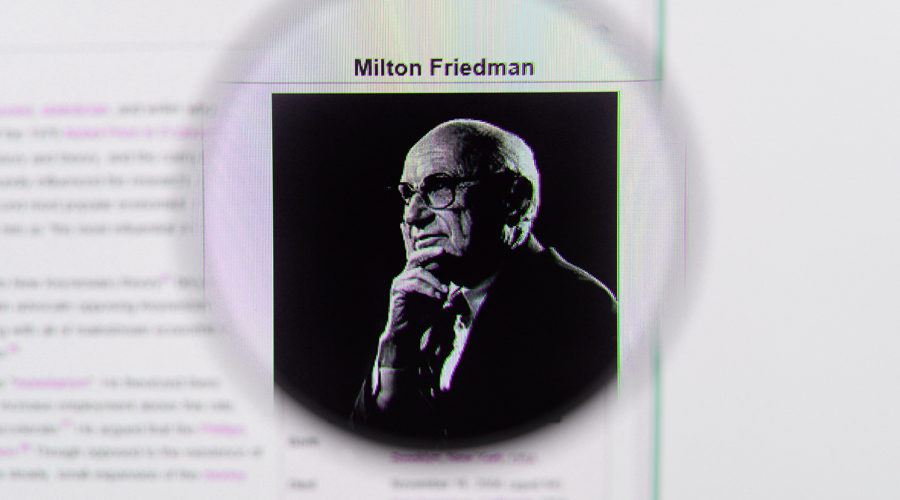
那个熟悉的、闪着微光的幽灵在房间上空盘旋了一两分钟,然后离开了,又重新出现了一会儿,然后消失了。
“在某种程度上,当两个人的行为影响到第三方时,政府总是存在的,”报告称。“有…例如,排放控制的案例。”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06年去世,在他去世近10年后描述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建立了声誉,使他赢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成为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守护神。
但与经常提到他名字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茶党(Tea Party)高论者不同,弗里德曼并不认为市场是一种无所不知、无需政府干预就能运作的力量,他也不反对环境立法。他反对的是指令与控制式的监管,这种监管规定了针对复杂和不断演变的挑战的狭隘解决方案,他喜欢的是比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那些简单化的口号更微妙的东西。
因此,前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鲍勃·英格利斯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让弗里德曼重新开始回答这个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会对气候变化做什么?”
使用视频节选的弗里德曼摔跤与20世纪的挑战,他们引发了深刻的,信息,甚至娱乐经济的辩证污染和沟通的艺术理论家——创建过程介绍经济学的“外部性”,Friedman称,他说,“两个人做的事情影响第三方。”(污染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
在他的第一次亮相中,虚拟弗里德曼为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棘手问题提供了他的解决方案。
他说:“(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最好的办法是对汽车排放的污染物征税。”“这使得降低污染符合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自身利益。”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Harri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助理教授史蒂夫•奇卡拉(Steve Cicala)随后用一个假设把我们带入了弗里德曼结论的逻辑。让我们假设,他说,他拥有一家钢铁厂,以每吨100美元的价格销售产品。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小组成员之一、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住在他所在工厂的下风处。
“我必须烧煤,而[格林斯通]有哮喘,”Cicala说。“所以,每生产一吨钢铁,他的健康就要花费20美元。”
污染是盗窃
Cicala对这种情况的道德性毫不含糊:“我对其他每一个输入供应商都进行补偿,”他说。“我得买煤。我必须买钢铁。所有这些交换都是基于互利的、自愿的交换,但我对迈克尔造成的污染是没有市场的。”
如果他不赔偿格林斯通的损失——而且是以格林斯通同意的方式——那么Cicala说他不是资本家。他是一个罪犯。
他说:“不付款的公司是偷窃罪。”“如果有人有更好的方式来描述未经他人同意、不赔偿他人的行为,我很乐意使用这个词。”
Inglis,一个理性的共和党人被驱逐的他还特别提到了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对美国总统奥巴马(mitt romney)的批评碳排放税因为它会提高能量速率。
格林斯通说,州长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因为温室气体“正在孟加拉国、洛杉矶、休斯顿、甚至佩里州长工作的奥斯汀的破坏区四处喷洒。”
而且,与Cicala的工厂不同,这不是一个假设。
“这些代价是真实的,”他说。“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我加油或开灯的价格中。”
所以,是的,佩里关于能源成本的观点是正确的——至少在短期内,对直接的消费者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他拒绝为“那些只顾自己的事情,让气候变化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无辜的人”付出代价,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格林斯通接着提醒我们,外部性不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这是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他说。“这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想法。”

烟囱
为什么不干脆禁止呢?
那么,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让污染者付钱上,而不是通过一项法律来禁止某些污染物或制定标准呢?弗里德曼的幽灵回来了,带着一个答案:
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调整机制,使我们能够适应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当然,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系统,也就是价格机制,它成功地引导我们在几个世纪里从木材到煤炭、鲸油、石油到天然气。”
他说,这种机制比指挥和控制更有效,因为它推动的解决方案是我们从官僚作风上永远无法预料到的。绿岩全心全意地同意了。
他说:“价格体系目前在能源体系中不起作用,正是因为碳排放被定价为零。”“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企业将很难筹集资金推出新的能源创新产品。”
然后他再次提醒我们,这并不是什么疯狂的想法,因为200位最常被引用的气候科学家中有98%都是如此同意气候变化是真实的(尽管气候科学的否认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反驳我们),所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对碳定价(PDF)。
“关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媒体总是报道科学家们近乎一致的观点,这真的很了不起,”格林斯通说。“从弗里德曼开始,到你能找到的最左翼的经济学家,人们达成了更大的共识,认为最正确的公共政策解决方案是给碳定价,但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他可能夸大了对碳价格的共识,尽管他后来指出,所有的监管都有一个价格;只是对特定污染物的明确价格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如何设定价格?
Cicala表示同意,然后提供了设定明确碳价格的两种最常见方法。一个方法是总量管制和交易,该协议为允许的排放量设定了上限,并允许价格波动。另一种方法从一个价格开始,让它来驱动数量。
他说:“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限制排放与交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定义排放到空气中的碳的数量,这是毫无争议的。”“然后,通过交易,我们会弄清楚……(减少排放)成本最低的方法。(在这种方式下)我们不太确定价格是多少,但我们肯定数量。”
第二种方法——从价格开始的方法——本质上相当于征税,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可以发出一个明确的、可能是长期的价格信号,让企业知道,寻找气候解决方案是值得的。
英格利斯说:“但人们担心税收会继续上涨。“如果你开始以这个价格征税,那么它能涨到多高?”
格林斯通承认了这一点,并提出了一个从“碳的社会成本虽然这并没有给受害者一个发言权,但这是向正义迈进了一步。问题是:你如何确定这个价格?
“这方面有新兴的科学,”他说,并引用了关于农作物产量骤降的影响和其他结果的研究。
“美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官方数字,”他说。“每吨37美元。这将为如何设定税收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导方针,也将是一种方式,可以限制淘气的国会对税收的手脚,防止它为了满足政治目的而上调或下调税收。”
在之后的讨论,他说,没有嵌入的环境退化成本生产成本相当于每年近24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行业,很多他的舍入美国排放了60亿吨一年,乘以每吨40美元。
他说,“我不认为其他经济领域有任何东西得到了这样的补贴。”
(顺便提一下,欧盟委员会也提倡一个基于转换到低排放技术的成本的固定价格。目标价格为每吨30欧元。)
如何实现它?
虽然这一切在理论上听起来很棒,但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固定的价格呢?
Cicala说:“如果我们是第一个实施征税的国家,那么碳密集的污染就会转移到海外。”他提出了“边境调整”的想法,即“根据碳含量对抵达美国的货物征税。”
英格利斯接着说,对他来说,没有边界调整的税收是不可取的。
他说:“如果我还在国会,而且碳排放税是不能调整边界的,我就不会因为刚刚发现的问题而投票支持它。”“我们将成为双重输家。我们失去了就业机会,也失去了减少排放的努力。然后,在国内,有些人会反对任何在某一领域增税而不在其他领域减税的做法。”
然后,他指出,他现在领导的保守的能源与企业倡议组织,联合主办了这次活动,认为任何碳排放税都应该是“财政中立”的,这“意味着在其他地方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减税”。他说,如果我们增加一项碳排放税,那么我们就必须减少另一项税收,以防止政府变得过于庞大。他用令人振奋的内省问其他人,“这是由经济学所暗示的,还是仅仅是我的保守哲学来承担?”
在这里,他们有些挣扎——一边谈论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机会,一边提高一种纠正市场扭曲的税收,但不直接承担给予石油行业的扭曲性补贴。
抵消和其他丢失的组件
他们设法在极短的时间内覆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片领土,但在讨论中漏掉了两个明显的因素。
一个是含蓄的:你可以从他们的其他声明中看出,这些先生们厌恶对石油部门的补贴。然而,另一种是他们唯一回避的:即,如果这是一种税收,特别是如果收入中立是“势在必行”,如英格利斯所说,钱怎么办?
如果收入中性意味着你可以削减所得税,那岂不是违背了以社会成本为基础征税的目的?毕竟,如果碳排放税的收益最终只是用来资助所得税的削减,那么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们又该怎么办呢?格林斯通在随后的讨论中提到了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移,但当通过限额交易筹集到的资金直接用于其他地方的减排项目时,该组织从未提起过抵消的话题。我相信我会在网上从Cicola和Greenstone找到一些很棒的东西,但如果能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就太好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题外话,他们谈到了美国领导力的重要性——这是美国在全球所做的事情,共和党在国内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你也可以辩称,正如格林斯通所暗示的那样,迄今开发的全球“解决方案”存在严重缺陷,但它们并没有真正解决现有的全球措施,也没有从它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走向全球
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关于边界调整的讨论实际上变得相当吸引人,特别是当Cicola提出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发起挑战的想法时。在他的设想中,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碳排放税将被其在原产国征收的同等税率所抵消。
“这给了其他国家更多的购买动力,”他说。“因为如果我开始从中国或印度的碳排放上征税,他们会想要分一杯羹。”
如果这些国家不这样做征收碳排放税对自己出口的产品?
“我们有机会在不参与的情况下从其他国家获得大量收入。”
如何销售?
在书的最后,Inglis提出了一个很接近他内心的想法:如何让右翼的理论家相信气候科学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需要解决它。他提供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慢慢地建立一个理性的保守派部落,这些人现在太害怕提高他们的声音,以免哈特兰研究所的蠢人嘲笑他们;另一种方法是从最终目标开始——也就是说,从这样一个信息开始:我们可以解决这一乱局,而不产生那种没有人真正想要的臃肿的官僚机构。
Cicola和Greenstone对第一点很赞同,但对过分推销第二点持怀疑态度。虽然格林斯通承认奥巴马政府目前的气候策略是一团糟,但他指出,这是一种必然的混乱。他说,也许现在是共和党人提出一个基于碳价格的真正计划的时候了——这个计划将比由于他们自己的固执而造成的混乱要好。
然而,他们都不遗余力地提醒我们,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是一种策略。这是一个幻想。在认识到政府效率低下的代价的同时,Cicola提醒我们,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特别是考虑到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说:“如果我们要在文明灾难和政府效率低下之间做出选择,我愿意接受政府的低效率。”
“认为市场是独立存在的,这是一种幻想,”格林斯通补充道。“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政府为它们的运作制定了基本规则。”
本文最初发表于生态系统市场。天安门广场图片由axz700 /在上面。




